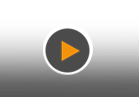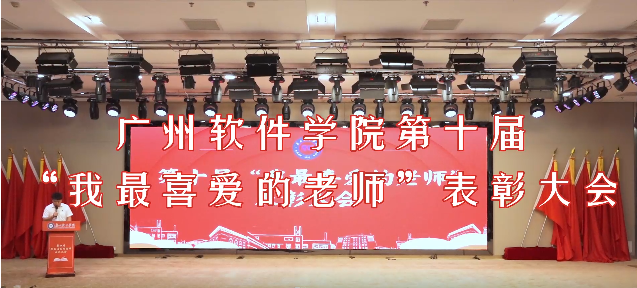现代诗人、散文家徐志摩在民国时期创作的散文集《迎上前去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,碎成断片,烂成泥,在这灰、这断片、这泥的底里,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、更光明的理想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。”印象中的徐志摩,一直以为他的内心是孤独地存放着浪漫和风骚,谁知他也在忧伤的花园外面徘徊着。
徐志摩,这三个字在当时的文坛被视为时髦、欧化的字符。一提起徐志摩,便让人联想起他短暂的一生,在张幼仪、陆小曼和林徽因三位女性中演绎的凄美故事。他让人感觉是风流倜傥的才子,在才子之余,又让人感觉他那出类拔萃的才气消逝得过快,只留下淡淡的挽惜。最初接触“徐志摩”这一名字,是在读了《再别康桥》那依依惜别的诗句: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。”那个时候,我就对康桥充满美好的幻想,对了解徐志摩的好奇心欲发强烈。而他笔下的康桥,就好像是一个穿越时光的故事,一对遥望梦想的目光,一双翱翔天空的翅膀。
此后看到康桥或剑桥大学相关的书籍,我便联系起徐志摩。总觉得康桥仿佛就是徐志摩的专利,而徐志摩就是康桥年轻而又古老的目光中熟悉的中国人。事实上,他在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中曾经理直气壮而激情地说道:“康桥的灵性全在条河上:康河(River Can),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。”似乎在他的生命里,康桥就是他心境的影子,涉笔于缥缈灵魂的梦园的最深处,一如康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和富有灵性。
徐志摩给人的感觉,在轻浮之余又带着几分浪漫主义的偏激。这偏激在他于一九二五年游历欧洲、莫斯科后思想态度和主观意识遭到自己狭隘个人主义的攻占。而我以为,徐志摩一生文采飞扬的年华,就是这种偏激伴随着他,直到一九三一年的飞机出事化为灰迹,实在令人惋惜。
谈到徐志摩,让人想起罗素。徐志摩对罗素有一种执着的感情,这种感情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他到英国来学的目的。对于罗素不确切的死耗,徐志摩又是掉眼泪又是做悼诗。单从这一事例,就可以断定他重感情,尊师之情可见一斑。当然,他在三位女性的圈子里徘徊得更直接、更大胆,或许他就是一位情感主义者。尽管他曾经宣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,尽管他的理想能否实现。
许多人说,徐志摩将理想尘封在他三位妻子的世界里,一如唐玄宗把江山断送在杨贵妃手上之说,这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。哲学里讲到,内因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,外因对内因只会产生影响和起到反作用。在这里,徐志摩是内因,三位妻子是外因,而他的理想还是理想,世界还是世界。
没有理想的人,就没有灵魂。没有灵魂,那么就像一个行尸走肉的人。可徐志摩两者都不是。让人感到惊讶的是,徐志摩曾经以《“使打破了头,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”》为题目尽情地阐述了自己的理想,自己的灵魂和自由。对于自由,他表达得淋漓尽致,是那样的坚定不移,即使牺牲了!
徐志摩的诗歌真实,真实得可以天马行空,还有那么一点飘缈。他的散文有血有肉,更有汗水。他是一位痛快淋漓的诗人,只因他不会珍惜自己,包括他的情感、相处、表达爱和自由,这些只能把它们概括为单纯。如果补充一点,那就是有些童真,他自己赞美儿童那种“烂漫的童真”的童真。
大抵是风雨兼程吧。徐志摩既热爱生活,又不会把握生活。这一点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和揣摩得到。我们只会“哈一下”的份儿,不算奇怪,就好像徐志摩是康桥遗失在草坪上游荡的魂灵,在眼睁睁地仰望着夕阳西落中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悲壮场面。而他对于康桥的热恋,一如荆轲的“头破血流”。后来,他对生活由赞美到轻视,由肯定到否定,就是那么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此情此景,令人感到一丝丝冷峻和惨烈!放眼望去,康河的水依旧潺潺地流动,流动着一颗永无归期的寂寞的心。
夜幕降临,我忽然想起水木年华《在他乡》的歌词。康桥,康河,在他乡,是否在还保管着徐志摩漂泊而疲惫的情愫,许多年过去了,依然让人想起那种潜意识的惋惜。
徐志摩的情愫,还有理想,在这灰中枯萎,在这断片中破碎,在这泥中腐烂,依然不失他执著的本色。